“爬上去照!”看着记者在给关门拍照,两个骑摩托车的过路人停下来,男的年纪四十多岁,女的不到三十,他们也是去看演出的。这个距山下乔沟5公里的平型关关口,原来的关门楼早已被毁。在八路军伏击日军时,这里曾经是国民党晋绥军抗击日军的战场。与关门附近残存的明长城残迹一样,几十年前的历史在这里,与几百年前的历史一样清晰可寻,却又同样模糊不清。
山下白崖台边的平型关大捷纪念馆最早是1969年由北京军区组织部队修建的,山顶高大的纪念碑在几公里外都清晰可见。灵丘县县志资料记载,“第一次展出期间,展厅内大量的图片、资料和当年八路军指战员的武器、用具,以及缴获日军的战利品,还有二楼展厅的大型电动沙盘,生动再现了当年平型关大捷的战况”。然而展馆只开了3个多月,很快就在1971年10月闭馆。“负责管理纪念馆的解放军奉命撤离,展品也全部撤走,后来这些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大部分被破坏或散失了。”1986年8月11日,亲自参加并参与指挥了平型关大捷的聂荣臻元帅批示山西省拨款修复纪念馆,但除了当年的一座巨大的毛主席半身像,绝大多数当年历史文物已寥寥无几。
有人指责中国人的记忆太具功利性,平型关的现状似乎从某种程度无奈地证明了这一点:看热闹的当地人没有人说得清、也没有人关心发生在60多年前本地最值得骄傲的历史,反倒是当年战场边的关帝庙在采金人的捐助下得以修复,至今香火不断。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在战后30年重返西班牙时曾经问自己:“他们是否还记得我所记得的那段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内的一面墙上,用文字、照片和画像,完整记录介绍了当年八路军115师参战部队所有营级以上干部数十人。名字正是历史中最重要的细节之一,因为他不可能有任何想象和改动的空间,也最容易经过历史的洗礼而保留沉淀。
武汉会战背景下的七天
1938年2月14日:武汉政治舞台上的周恩来
记者◎李菁 特约记者◎雷静
周恩来的新角色
2月14日,冯玉祥在武汉的寓所里,接待了一位特殊客人——周恩来。
一个星期前,周恩来通过冯的部下鹿钟麟向冯玉祥表示:拟请一见。根据冯玉祥的秘书整理的《冯玉祥日记》记载,冯对这个提议最初还颇有些顾忌,他让鹿钟麟转告:“因外间耳目众多,不便相见,惟努力作不见面之默契可耳。”但不知为何,冯玉祥又很快改变了想法。
据《周恩来传》记载,周恩来与冯玉祥主要交谈了对时局和抗战前途的看法,“谈得很畅快”,特别是对前一段华北和上海作战指挥的得失进行详细的探讨。当时担任冯玉祥秘书的于志恭回忆,周恩来也向冯介绍了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精神,“深得冯先生的赞许和拥护”。
“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当天晚上,冯玉祥在日记里这样描述周恩来。看得出,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给冯玉祥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于志恭回忆,在周离开后,冯玉祥就对周围的人连连感慨:“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第二天,冯在自己的会客室写下八个大字:“吃饭太多,读书太少。”表示自己不如周恩来。
周恩来自此与冯玉祥开始了近10年的交往,“以后,他常派他的专车将周恩来接到寓所晤面”。
周恩来是在1937年12月18日,与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邓颖超一起从延安到达武汉,与先期到达的叶剑英等人汇合。此前,中共方面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及叶剑英组成代表团驻武汉,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
一个星期之前,还有一个月就满40岁的周恩来在武汉出任了一个新职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当国共两党为了共赴国难再度走到一起时,在国民党中也享有较高声望的周恩来顺其自然地成为了担任这一历史使命的最佳人选。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恢复北伐时期军中的政治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并邀周恩来担任副部长——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当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陈诚还只是一个炮兵队长,深知“辈分”的陈诚亲自登门相请;同时,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通过国民党元老、副院长张群出面,邀请周恩来到行政院任职。对这两项邀请,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以“担心引起两党摩擦”为由,婉言推辞。但在蒋介石的一再坚持下,周恩来同意出任。在这个平台上,周恩来很快利用他的个人魅力与早期结识的国民党上层,迅速而游刃有余地进入新角色。
几天后,周恩来又受白崇禧之邀,为路过武汉、马上开赴前线的广西学生军作讲演。白崇禧是国民党将领中的主战派,同周恩来经常见面。一个月后,奉派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时,白崇禧在临行前特地把周恩来和叶剑英请到家里,请教对敌作战方针。据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回忆,10月25日凌晨从武汉撤退时,周恩来正巧看到全身戎装的白崇禧站在路边,原来是他的吉普车因故障抛锚正在修理,周恩来马上下车对白说:“敌人骑兵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远,赶快上我的车去长沙吧!”白崇禧于是坐上周恩来的车一同走了,“两人在车上作了较长时间的交谈,从个人出身到国共合作、抗战形势等无所不谈。”童小鹏说,当时白崇禧还笑着对周恩来说:“你们(共产党)未到我们广西,我很感激!”而周恩来也不失时机地对白崇禧等桂系军阀的一些做法表示肯定。
此时的周恩来,也代表了经过十年内战的长期隔绝状态后,重新向外公开接触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在此之前,中共同苏联以外的国际社会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只有埃德加·斯诺等很少几位外国朋友到过陕北,向国外作了报道。
武汉的“文艺复兴”
1938年2月14日,周恩来亲自邀请老舍,希望他出面将流亡到武汉的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1937年11月,在山东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别妻离子,从济南只身流亡到武汉。他曾说过:“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的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
那时的武汉聚集了来自全国的文化名流,有胡风、萧军、萧红、沈从文、丰子恺、郁达夫,赵丹、金山、舒绣文、冼星海、崔嵬等,他们因上海的沦陷而流亡至此。他们的到来使武汉也成了全国的文化中心。
老舍接受了周恩来的提议和邀请。经过老舍和阳翰笙等的筹备,一个月后,“文协”开幕大会召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为总主席,周恩来、蔡元培、罗曼·罗兰和史沫特莱等13人被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
在“保卫大武汉”的紧张空气中,此刻的文协成立大会上,却出现了难得的热烈与和谐场面。被推举为文协理事的冯玉祥还兴致勃勃地上台表演文艺节目。“轮到他表演时,他趋向台前,轻拂着一块手绢,大唱泰山民歌《柴夫的儿子》,博得满堂喝彩声。”于志恭回忆。会后,冯玉祥在普海春大饭店设宴招待与会的全体文艺界人士,五六百位文艺界人士欢聚一堂,谈着团结抗战的话语,那种团结向上的热烈气氛,即便是十年后冯玉祥在异国他乡回忆起来,仍留恋不已:“在武汉这一个地方,最好的现象是大家都想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如同汉口成立的抗敌文协,是舒舍予(老舍)他们领导的。我听说,这些拿笔杆子的文人,平时都是你挑剔我,我批评你,谁和谁都不易在一起;这一次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雪我们全民族的耻辱,他们成立了抗敌文协,大家全团结起来了,把自己互相指责的精神,集中起来对准敌人进攻!”
“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周恩来发表了一番热烈的演讲。
5月中旬,周恩来被邀请到文协参加第二次理事会。老舍后来在会务报告中对这次会议有一次生动的描写: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儿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眼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极富感染力的周恩来让这些文艺工作者充满了敬佩之情。后来,不少作家和文艺工作者都选择了共产党,为了吸收革命青年,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也帮助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招生,据“八办”提供的材料,“仅以1938年5月至8月的记载”,这一数字已达880人之多。“1938年8、9月武汉形势吃紧后,党组织加紧动员大批工人、学生和其他人去延安,常常是以集体的形式,二三十人,五六十人乃至百余人,大批大批地出发奔赴延安。”周恩来的个人魅力,应该在其中扮演不小作用。
在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大敌压境之前的武汉出现了短暂的文化兴盛现象,以致郭沫若一度认为抗战的武汉时期可谓中国的一个“文艺复兴期”。
周恩来组建的“名流内阁”
这一天,郭沫若仍在长沙静静等候着周恩来来自武汉的最终决定。
1938年1月,携着在上海结识不久的于立群,46岁的郭沫若来到武汉。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流亡日本近十年的郭沫若“别妇抛雏”,秘密潜回中国,并在上海结识了小他二十几岁、艺名黎明健的左翼女演员于立群,上海沦陷后,郭沫若与何香凝、邹韬奋等先到了广州,后又辗转至武汉。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设四个厅,初到武汉的文化名人郭沫若成为蒋介石期望的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的人选。对于这一提议,郭沫若起初并不愿接受,认为到第三厅是帮蒋介石的忙,后索性离开武汉到长沙“躲避”。据《周恩来传》介绍,三天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郭做工作,郭沫若终于同意,“但希望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公开地、痛痛快快地工作”。周恩来又劝他以非党人士身份,忍住内心的“寂寞”为好,郭沫若最终以“文化人士”的身份出任第三厅厅长。
1938年4月1日,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昌昙华林成立。67年之后——2005年5月21日,记者在武汉采访时,重新踏访了第三厅的旧址。位于武昌的昙华林路是条悠长而略显逼仄的小路,几经打听,我们才找到隐于这条窄街上的武汉市第14中学。
在一片绿色当中的一座二层的红顶小楼,静静地立于充满现代感的塑胶场地的另一端。“它见证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也见证了文化名流聚集于此、团结抗战的历史。”蒋校长一边带我们登上这座已有些斑驳的小楼,一边向我们介绍。蒋校长说,解放后,这座二层小楼曾被当作学校的教工宿舍,直到“文革”后这个革命旧址重新被重视,老师们搬出来,小楼单辟成纪念室。
其实,这里最初是政治部本部的工作地址,郭沫若后来在《洪波曲》中写道,因为要经过一条很窄而长的背街才能到达,那条背街只能够勉强通过一部汽车,“大员们嫌交通不便,不久便乔迁了”,所以第三厅得以“独占”于此。包括阳翰笙、傅抱石、田汉、徐悲鸿、史东山、光未然、冼星海等著名文化人分别担任各项工作,可谓人才济济。
“那是星期天的早上,我和父亲从江汉关坐船到了武昌。黄鹤楼一带从马路一直到几百级的台阶上,全都挤满了人。”1927年出生的徐明庭老人至今仍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年参加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的情景,那时11岁的徐明庭还是特三区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这个活动是由第三厅组织发起的。作为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实际上也将大部分精力倾注到三厅的工作当中。
对普通武汉人来说,周恩来、郭沫若都不是陌生的名字。“那时武汉的报纸经常宣传他们”。致开幕词的郭沫若充分发挥了他富于激情、感情充沛的诗人特长;郭沫若之后是周恩来的讲话,“周恩来分析抗战形势,从东北、华北到华中,每个地方他都非常熟悉,讲起来也头头是道,下面的听众非常专心地听他的讲话。”最后一项是冼星海指挥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那时这些歌在武汉非常流行,学校老师也教我们唱抗日歌曲”,“国难当头,大家好像通过这种形式把胸中对侵略者的愤恨都表达出来”。
数十万群众从黄鹤楼出发,沿武昌主要街道开始游行。队伍最前面是孙中山遗像,然后是国共抗日将领的画像,许多人举着用纸扎成的坦克或飞机形状的彩灯,没有彩灯的人则手举着火把。游行队伍经过的街道,旁边的群众鼓掌或与其一起大合唱,也不时有人举着火把加入。
“我和父亲跟着队伍走,一直到阅马场附近。汉阳门江边上停了很多船,合唱队全部上了船,冼星海在船上指挥大家继续唱,船在江上游行,岸上的人也在配合跟着合唱。”沉浸在往事回忆中的徐明庭老人,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着那个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火炬、彩灯绵延不断,歌声从这船传到那船直上云霄,我们都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倦。”
这个活动也是周恩来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军委员宣传工作打响的第一炮。当外界为周恩来的风采倾倒时,身边的工作人员童小鹏却见证了他的辛劳。因为政治部设立在武昌,周恩来住在汉口,“他每天上午9时前就要过江赶到武昌政治部上班,或进行统战活动,晚上又要过江回汉口来,处理许多急于处理的事情”。因此,处理中共内部事务的会,经常不得不在半夜召开,有时到凌晨才能结束。
“董老(董必武)年纪较大,会开得太晚他常常要在躺椅上打个盹后再起来继续开会。”童小鹏当时任周恩来的秘书兼机要科长,白天忙完整理记录、传阅电报这些杂事已经很累了,“所以一到晚上开会做记录就常常打瞌睡”,有时第二天起来整理头天晚上写的会议记录,自己都认不得了。
初展外交风采
1938年的2月14日恰好是农历元宵节。上午9时许,三架日机飞临郑州上空,接连不断地在繁华地带投掷数枚炸弹,将正在观看舞狮、旱船、龙灯、高跷的市民瞬间推向死亡。
如今的汉口长春街57号便是当年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旧址。这座青灰色的四方形建筑粗看有些单调,进入门里细细观看却发现也别有特色。工作人员介绍说,南京沦陷后,南京“八办”并入武汉“八办”。原在汉口府西一路(现民意一路)安仁里的房子便不够用了,经董必武和叶剑英与汉口市政府协商,将原日租界的日商大和洋行拨给“八办”。
严格说起来,这个旧址也并非当年周恩来等人所在的“武汉八办”——1944年,这幢房子在美机轰炸日本时严重受损,直到1978年才按原样修复。按原来的设置,楼上某层也分别是陈绍禹(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博古)的房间,但王明的房间是紧锁的,工作人员说,因为王明后来的“政治错误”,这个房间一直是不对外开放的。
当年这座建筑见证了我们后来非常熟悉的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1938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此会见了由加拿大共产党委派的白求恩医疗小组,经周恩来介绍,白求恩从这里到达延安;8个月后,来自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也到达“八办”并在屋顶花园举行了招待会,并在此与周恩来见面。
“他侃侃而谈,精力充沛,学识渊博,长着一对机灵、谨慎的眼睛,还有中国少见的浓眉。”与柯棣华大夫一同前来的巴苏,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便为他折服,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下午,我们去看望周恩来,他正在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大部分是外国人。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倾听着他透彻地分析中国的军政局势,以及阐明怎样通过全国发动群众抗击敌人。”周恩来给这几位国际友人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的忙碌,“看来他好像连每天刮脸的时间都没有”,“电话和通讯员不断地打扰着招待会”。“见到我们,并得知我们要去八路军那儿,他显得非常高兴。他说八路军将会给我们最热烈的欢迎。”
几天后,巴苏与柯棣华再一次见到周恩来。巴苏后来在日记里满怀敬意地写道:“在爪哇支队举行的盛大宴会上,我们全体再次见到了叶剑英和周恩来。”“在全体来宾中,周恩来是惟一庄重的人,我有机会从很近的地方观察他。他吸引我的,是他那机敏、聪慧和富于同情感的目光。安娜(注:德国友人安娜利泽)说,20年后,我们将会为曾经与他结识感到骄傲。我补充道:‘干吗这么晚呢?此刻我们就感到骄傲。’”
1938年10月25日凌晨,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社口授了在武汉出版的最后一期社论之后,率领长江局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离武汉,也把一个近乎完美的形象留在了武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研究员为本文提供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致以衷心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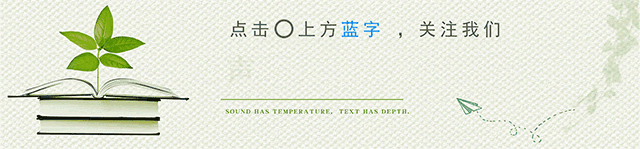




发表评论: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